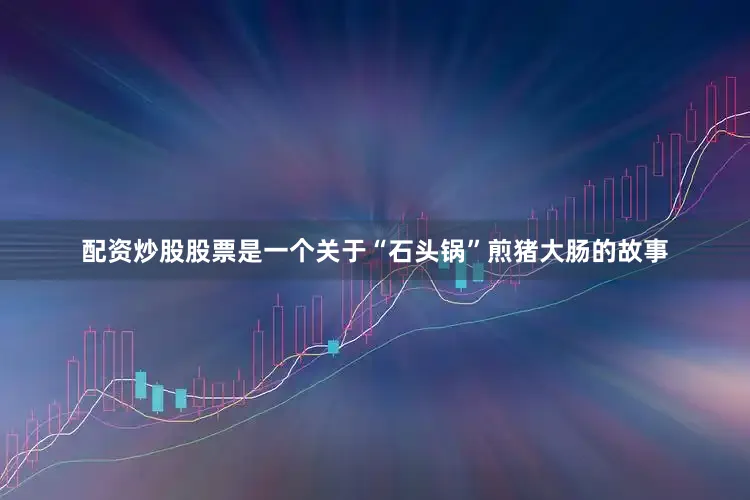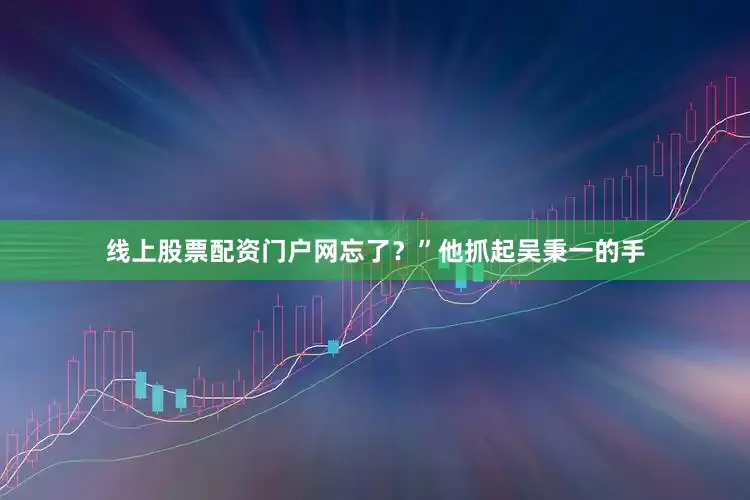
第二章:交易!双枪赌命
小磨山西坡的断墙后,山风卷着松涛声,把牛子龙的烟卷吹得明明灭灭。他刚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油纸包,就被吴秉一劈手夺了去——里面四个白面馒头还带着余温,麦香混着酵母的甜气,勾得人喉头直动。
“你嫂子凌晨三点起的面。”牛子龙靠在断墙上,额角的月牙疤在阳光下泛着浅红,“知道你这群弟兄,怕是有日子没见过细粮了。”
吴秉一没说话,掰了半块馒头塞进嘴里,嚼到第三下就停住了。他认出这手艺——当年在郏县师范,牛子龙的妻子总给学生们送馒头,酵母里掺着点槐花蜜,甜得能让人忘了饿。可现在这甜味里,却裹着股说不出的涩。
“韩六谦把你哥嫂关在县大牢最里头,”牛子龙突然开口,烟蒂往地上一摁,“门口守着一个排,你那点人冲过去,不是救人,是送命。”
吴秉一手里的馒头“啪”地掉在地上。他想起兄长修鞋时总哼的《小放牛》,想起嫂子纳鞋底时念叨的“等秋收了换头驴”,这些画面突然被韩六谦那张肥脸撕碎。“那我就眼睁睁看着?”他的声音发颤,手不自觉摸向腰间——那里还别着从狱警手里夺的空枪。
展开剩余70%牛子龙从怀里摸出张照片,泛黄的相纸上,穿日军少将制服的男人正用军刀挑着婴儿襁褓,背景里的郏县祠堂烧得只剩骨架。“吉川贞佐,天皇外甥,”他用烟卷点了点照片上的人,“上个月在薛店镇,活埋了三十个乡亲,包括你娘。”
吴秉一的呼吸猛地顿住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银镯子还硌在胸口,那冰凉的触感突然变得滚烫——就像那天她倒在日军刺刀下时,溅在他手背上的血。
“杀了他,”牛子龙的声音压得极低,“军统能给你撤通缉,能逼韩六谦放人,还能给二十万买枪买粮。”他忽然冷笑一声,“顺带让日本人跟国民党狗咬狗,咱们坐收渔利。”
“你说啥?”吴秉一猛地站起来,断墙的土块被他踩得簌簌掉,“中国人打中国人还不够,还要借鬼子的手?先生当年教我们的‘民族大义’,都喂狗了?”
牛子龙也火了,从帆布包里翻出个铁皮盒,摔在吴秉一面前。盒盖弹开,露出张卷边的黑白照——十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举着“还我河山”的木牌,前排左三是梳着分头的吴秉一,右二是穿着蓝布长衫的牛子龙,两人的胳膊紧紧挽在一起。
“这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学生运动,”牛子龙的声音发哑,指着照片里被警棍打破头的学生,“那天你替我挡了一棍,额角缝了四针,忘了?”他抓起吴秉一的手,按在自己手腕的枪伤上,“我这疤是打刘兴周时留的,他卖国求荣,管他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,都是该杀的东西!”
吴秉一盯着照片上自己青涩的脸,突然说不出话。那年牛子龙把薪水全买了进步书籍,夜里在油灯下教他们认字,说“枪杆子能救国,笔杆子也能”。可现在,这双手既握过笔,也沾了血。
牛子龙忽然从帆布包里掏出两把二十响驳壳枪,扔给吴秉一。枪身泛着蓝光,还带着枪油的腥气。“试试。”
吴秉一接住枪的瞬间,拇指已经拨开保险。他闭上眼睛,指尖在枪身游走,卸弹匣、拆枪管、卸撞针,零件“叮叮当当”落在掌心,不过三秒又重组归位。最后“咔”的一声推上弹匣,枪口稳稳指向十米外的酸枣树,枝丫应声而断。
“好小子,”牛子龙眼里闪过笑意,“当年教你的‘盲拆枪’没忘。”他忽然放缓语气,“吉川身边有个翻译叫陈凯,是自己人,但别让他知道你的底。”
吴秉一摩挲着枪身的烤蓝,忽然问:“事成之后,能保证我家人安全?”
“我以这道疤起誓。”牛子龙指着额角的月牙疤,“当年若不是你娘把我藏在菜窖,我早成了国民党的枪下鬼。”
吴秉一终于点头,伸手去接牛子龙递来的吉川照片。指尖刚碰到相纸,突然瞥见背面的字迹——“你妻儿被关在开封狱,韩六谦的人守着”。
“嗡”的一声,他的手指猛地一颤,二十响驳壳枪突然走火。
“砰!”
子弹穿透照片上吉川的额头,打在断墙上迸出火星。硝烟散去后,相纸上的弹孔正对着吉川那双阴鸷的眼睛,像个血窟窿。
吴秉一盯着弹孔,喉结滚动着。他想起儿子周岁时抓周,一把抓住了他的玩具木枪,妻子笑着说“随他爹”。现在那木枪怕是早被韩六谦踩碎了,就像踩碎了无数个家庭的日子。
“开封城的路,我熟。”他把照片揣进怀里,枪身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,烫得胸口发疼,“三天后,给你信。”
牛子龙看着他转身的背影,忽然喊了句:“保重。”
吴秉一没回头,只是举起枪,对着天空扣动扳机。枪声在山谷里荡开,惊飞了一群灰雀,像撒出去的一把希望,往开封的方向去了。
发布于:河南省欣旺配资-股票配资网址-场外股票配资-实盘配资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